来源:《诗刊》2024年第1期“百家诗论”栏目

上世纪70年代,叶嘉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南开大学供图
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
叶嘉莹
谈到我国旧诗演进发展的历史,无疑唐代是一个足可称为集大成的时代,只根据《全唐诗》一书来统计,所收的作者,就有二千二百余人之众,而所收的作品,则更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之多。在如此众多的作家与作品中,其名家之辈出、风格之多采,自属一种时势所趋的必然之现象。面对如此缤纷绚烂的集大成之唐代诗苑,如果站在主观的观点来欣赏,则摩诘之高妙、太白之俊逸、昌黎之奇崛、义山之窈眇,固然各有其足以令人倾倒赏爱之处,即使降而求之,如郊之寒,如岛之瘦,如卢仝之怪诞,如李贺之诡奇,也都无害其为点缀于大成之诗苑中的一些奇花异草。然而如果站在客观的观点来评量,想要从这种种缤纷与歧异的风格中,推选出一位足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则除杜甫而外,实无足以当之者。杜甫是这一座大成之诗苑中,根深干伟、枝叶纷披、耸拔荫蔽的一株大树,其所垂挂的繁花硕果,足可供人无穷之玩赏,无尽之采撷。
关于杜甫的集大成之成就,早自元微之的《杜甫墓志铭》、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赞》,以及秦淮海的《进论》,便都已对之备致推崇。此外就杜甫之一体、一格、一章、一句而加以赞美评论的诗话,历代的种种记述,更是多到笔不胜书,至于加在杜甫身上的头衔,则早已有了“诗圣”与“诗史”的尊称,而近代的一些人,更为他加上了“社会派”与“写实主义”的种种名号。当然,每一种批评或称述,都可能有其可资采择的一得之见,只是,如果征引起来,一则陈陈相因,过于无味;再则繁而不备,反而徒乱人意。我现在只想简单分析一下杜甫之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成就的主要因素。我以为其主要因素,实可简单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是因为他之生于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时代;其二,是因为他之禀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容量。
先从集大成的时代来说,一个诗人与其所生之时代,其关系之密切,正如同植物之与季节与土壤,譬如二月早放之夭桃、十月晚开之残菊,纵然也可以勉强开出几朵小花,而其瘦弱与零丁可想;又如种桑江边,艺橘淮北,纵使是相同的品种根株,却往往会只落得摧折浮海、枳实成空的下场。明白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更会深切地感到,以杜甫之天才,而生于足可以集大成的唐代,这是何等值得欣幸的一件事了。自纵的历史性的演进来看,唐代上承魏晋南北朝之后,那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段萌发着反省与自觉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纯文学之批评既已逐渐兴起,而对我国文字之特色的认识与技巧的运用,也已逐渐觉醒。上自魏文帝之《典论·论文》、陆机之《文赋》,降而至于钟嵘之《诗品》、刘勰之《文心雕龙》,加之以周颙、沈约诸人对四声之讲求研析,这一连串的演进与觉醒,都预示着我国的诗歌正在步向一个更完美更成熟的新时代。而另一方面,自横的地理性的综合来看,唐代又正是一个糅合南北汉胡各民族之精神与风格而汇为一炉的大时代,南朝的藻丽柔靡、北朝的激昂伉爽,二者的相摩荡,使唐代的诗歌,不仅是平顺地继承了传统而已,而且更融入了一股足以为开创与改革之动力的新鲜的生命。这种糅合与激荡,也预示着我国的诗歌将要步入一个更活泼更开阔的新境界。就在这纵横两方面的继承与影响下,唐代遂成为了我国诗史上的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在体式上,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而另一方面,它又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体式,使之益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在风格上,则更融合了刚柔清浊的南北汉胡诸民族的多方面的长处与特色,而呈现了一片多彩多姿的新气象。于是乎,王、孟之五言,高、岑之七古,太白之乐府,龙标之绝句,遂尔纷呈竞美,盛极一时了。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位作者,亦如孟子之论夷、齐、伊尹与柳下惠,虽然都能各得圣之一体,却不免各有所偏,而缺乏兼容并包的一份集大成的容量。他们只是合起来可以表现一个集大成之时代,而却不能单独地以个人而集一个时代之大成,以王、孟之高雅而短于七言,以高、岑之健爽而不擅近体,龙标虽长于七绝,而他体则未能称是,即是号称诗仙的大诗人李太白,其歌行长篇虽有“想落天外,局自变生”之妙,而却因为心中先存有一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成见,贵古贱今,对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作品,便尔非其所长了,所以虽然有着超尘绝世的仙才,然而终未能够成为一位集大成的圣者。看到这些人的互有短长,于是我们就越发感到杜甫兼长并美之集大成的容量之难能可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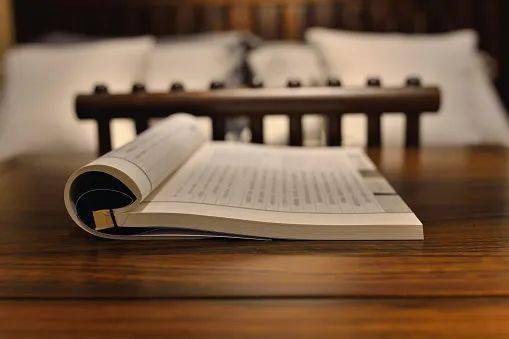
说到杜甫集大成的容量,其形式与内容之多方面的成就,固早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所以能有如此集大成之容量的因素,我以为最重要的,乃在于他生而禀有着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且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而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而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之外,做到博观兼采而无所偏失。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的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醉时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桃竹杖引》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自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则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
杜甫的继承传统与突破传统的精神,以及其深厚博大的蕴涵,表现于古近各体,都有其特殊独到的成就,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我以为该是他在七言律诗一方面的成就。因为,其他各种体式,到杜甫的时候,可以说大致都早已臻于成熟之境地,而唯有七言律诗,则仍在尝试之阶段。对于其他各种体式,杜甫虽然亦能有所扩展与革新,然而毕竟前人之作已多,有着足够的可资观摩取法的材料,而唯独对于七言律诗一体,则杜甫之成就,乃全出于一己之开拓与建立。如果我们把各体诗歌的成就,比作庭园的建造,则其他各体,譬如早经建筑得规模具备、完整精美的庭园。杜甫于进入园中周游遍览之余,一方面既能尽得前人已有之胜,一方面更能以其过人之才性,见前人之所未见,于是乎据山植树,导水为池,更加以一番拓展与改建,这种拓展与改建,当然也弥足珍视,然而毕竟可资为凭藉者多,拓建较易,而意义与价值亦较小。至于七律一体,则在杜甫以前之作者,只不过为这座庭园才开出一条入门的小径,标了一面“七律”的指路牌,而园门以内则可以说仍是旷而不整,一片荒芜,从辟地开径,到建为花木扶疏、亭台错落的一座庭园,乃全出于杜甫一人之心力。如果说在中国诗史上,曾经有一位诗人,以独力开辟出一种诗体的意境,则首当推杜甫所完成之七言律诗了。
而自诗歌之内容方面而言,则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态,他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郑虔博士之“樗散鬓成丝”,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李邓公骢马之“顾影骄嘶”,写东郊瘦马之“骨骼硉兀”;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则以上声马韵予人以一片沉悲哀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则以沉雄之气运骈偶之句,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含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其次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尝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之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之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一般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其最著名的《北征》一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囊空无帛、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态。又如其《空囊》一诗,于“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的艰苦中,竟然还能保有其“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诙谐幽默。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题中,则往往可见有“戏为”“戏赠”“戏简”“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杜甫的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正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此种优越之禀赋,不仅使杜甫在诗歌体式、内容与风格方面达到了集大成之多方面的融贯汇合之境界,另外在他的修养与人格方面,也凝成了一种集大成之境界,那就是诗人之感情与世人之道德的合一。在我国传统之文学批评中,往往将文艺之价值依附于道德价值之上,而纯诗人的境界反而往往为人所轻视鄙薄。即以唐代之诗人论,如李贺之锐感,而被人目为鬼才,以义山之深情,而被人指为艳体,以为这种作品“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涪《释怪》)。而另外一方面,那些以“经国”“奖善”相标榜的作品,则又往往虚浮空泛,只流为口头之说教,而却缺乏一份诗人的锐感深情。即以唐代最著名的两位作者韩昌黎与白乐天而言,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他们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仅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已。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恶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寻求,故其所得者浅;深厚自然之情则由于天性之含蕴,故其所有者深。所以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谕之诗,在千载而下之今日读之,于时移世变之余,就不免会使人感到其中有一些极浅薄无谓的话,而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则仍然是满纸血泪、千古常新,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并未因时间相去之久远而稍为减退,那就因为杜甫诗中所表现的忠爱仁厚之情,自读者看来,固然有合于世人之道德,而在作者杜甫而言,则并非如韩、白之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出于诗人之感情的自然之流露。只是杜甫的一份诗人之情,并不像其他一些诗人的狭隘与病态,乃是极为均衡正常、极为深厚博大的一种人性之至情。这种诗人之感情与世人之道德相合一的境界,在诗人中最为难得,而杜甫此种感情上的健全醇厚之集大成的表现,与他在诗歌上的博采开新的集大成的成就,以及他的严肃与幽默的两方面的相反相成的担荷力量,正同出于一个因素,那就是他所禀赋的一种博大均衡而正常健全的才性。
以杜甫之集大成的天才诗人之禀赋,而又生于可以集大成的唐朝的时代,这种不世的际遇,造成了杜甫多方面的伟大的成就。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则该是他的继承传统而又能突破传统的一种正常与博大的创造精神,以及由此种精神所形成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表现。

